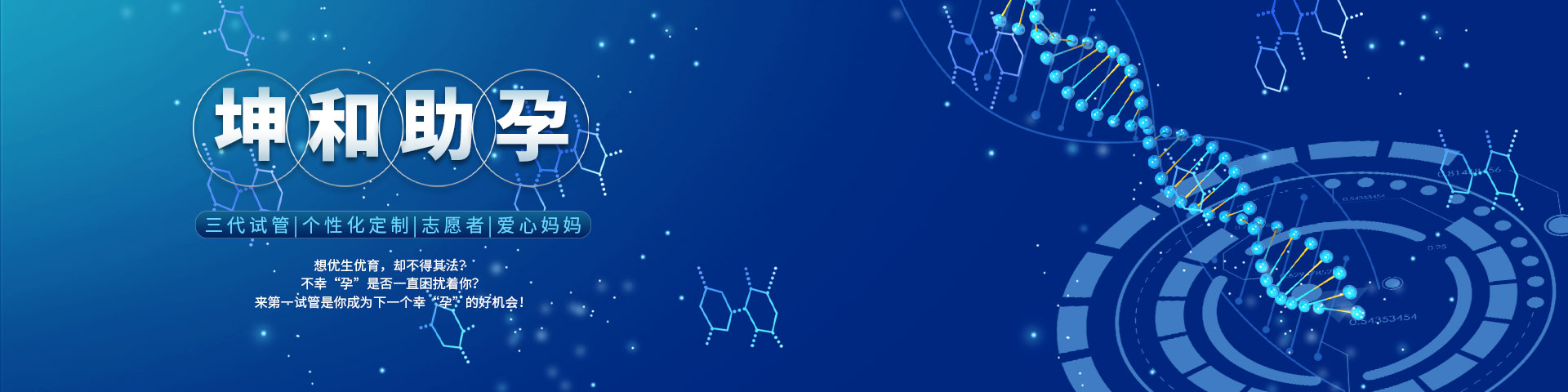年仅35岁的我,得了霍奇金淋巴瘤,因为发现的比较早,医生说可以通过化疗放疗治愈,但是对身体有极大的伤害性,通常卵巢也会受到影响,大小因人而异,有的人从此绝经,有的人卵子全部失去活性,也有人数年后会自我修复。总之「无法生育」是一个可能性非常大的结果,因此医生让我考虑一下冷冻卵子。
和全家人协商后,我最终决定冻卵,想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个选择。因为不知道 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过着什么生活,想不想要孩子,那几颗 35 岁的卵子至少是已知的、熟悉的存在,是一个确凿的后备计划。

冻卵其实并不是一次手术,而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过程——手术本身全麻,其实没有任何感觉。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来到了澳门坤和助孕中心的医生做远程会诊之后,医生为我排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打什么针,哪天上医院检查,诸如此类。整个过程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因为我是广州人,所以先是在广州做的相关检查。
我被安置在一个椅子上,像生孩子一样张开双腿;洗手台上放着
整整一罐白白净净的安全套,女医生掏出一个戴在一根根子上,就伸进我的阴道里戳来戳去,痒得不行。
抵达澳门后的,自己给自己打针也是有趣的,要像糖尿病人一样拎起自己的肚皮,狠狠地戳进去,再缓慢缓慢地把药水打进去。
医生说如果我实在不敢自己打也可以请其他人帮着打,但我觉得与其让别人抓住我的肚皮还不如自己来呢……药有时候打3种,有时候打4种,有些是配好的,还有一些要像以前用过的干粉和溶剂类型的美容保养品一样,需要每次自己调配,而且药物都要冷藏。

我在打针期间经历了一次搬家,坤和健康的服务人员还细心的准备了保温箱和冰袋,折腾了一番。
我第一次打针的时候,给我妈进行了视频直播。我紧张得手抖,她却觉得很可笑。
这么想来,我身边的人真是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呢。
手术当日其实和你简单,一早7点半就到了诊所,签署了一些同意书之后,进入手术区更换了手术服。同麻醉师和医生、护士进行了详细沟通,告诉了他们以前麻醉历史。就在医生告诉我别紧张,准备开始手术了之后,就迅速睡着了,直到被麻醉师唤醒了。
很舒服,最大的感受,真的,真想就这么一直睡下去了
大约休息了30分钟吧,麻醉师让我慢慢的坐起来,喝了点果汁后就去换衣服了。回来后,医生很开心的告诉我,一共取了12个成熟的卵子。12个啊,也许这其中就有一个是未来的宝宝呢。
护士用轮椅把我推出来一直到车上,有点轻微出血,护士也给准备了卫生巾,有一点点像来例假的感觉,但是不疼。只是超过12小时没有进食了,有点渴,也有点饿了。
虽然不能看见自己卵子的实体,但是医生给了我张照片:健康的卵子,圆圆胖胖,甚至还有点毛茸茸。
我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卵子」这种生物学上的概念,竟然一五一十地出现在我眼前,还是从我体内拿出来的。同时竟然也有了「这些就是我的孩子了」的奇特亲密感。
取出的卵子没有密码也没有号牌,只是和我的名字直接绑定,类似生下来的宝宝脚上栓上妈妈的名字……大概只能相信医生不会搞错了。
同时,由于我的卵巢前途未卜,自己也有些为那 12 个圆球感到可怜,觉得它们未来在冰库里暗无天日地生活着一定很孤独。
我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治病,对于生命的孤独也算有点小小的体会。

在大陆范围内,冻卵这件事的公众普及,很大程度上得归功到徐静蕾头上。听说一个月前徐老师在和别人聊起时,觉得自己冻卵有点上瘾。
我自己是没有这瘾的,这事儿的机会成本太高了。首先冻卵本身比较贵;其次在乐观的情况下,我已经获得了三次受孕机会,多冻也不会改变太多;更不用说假如卵子本身情况悲观,就更没有必要了(卵子的活性似乎和年纪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但我想徐静蕾谈论的上瘾也不是针对冻卵本身,而是这个给自己增加选择权、增加未来可能性的过程。于我而言,当我觉得我在给自己铺设一种未来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