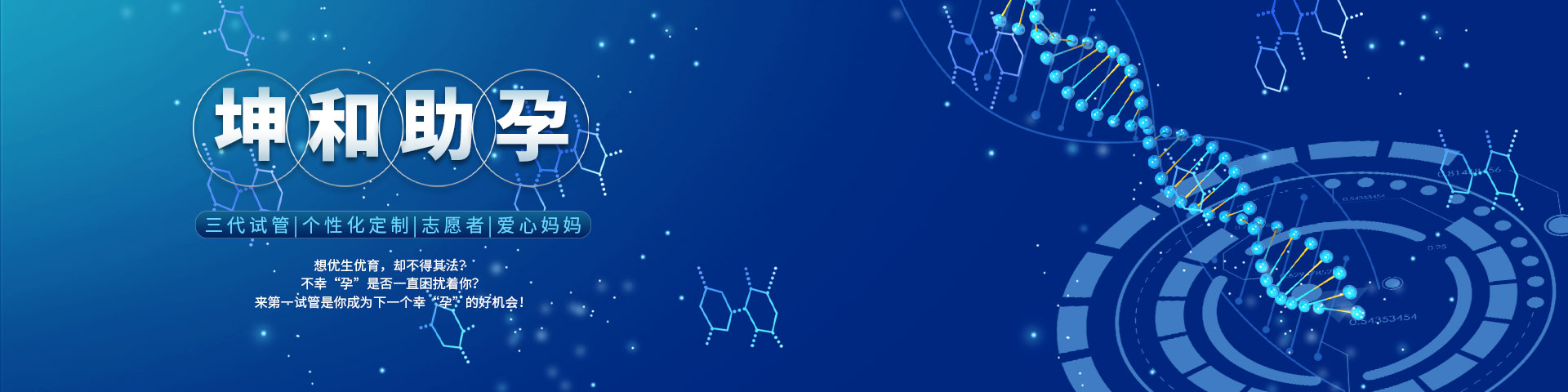近年来,不孕症的发病率逐年增加,加之适孕人群生殖能力下降,不孕不育不仅是一种身体疾病,而且也是目前全球性的复杂社会学问题之一。不孕症的患病率因地域、种族等有所差别,我国不孕症的发病率大约15 %。作为不孕症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 embryo transfer, IVF-ET)为主要代表的辅助生殖技术(artificial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在中国大陆已经实施了214年。至今,ART在技术本身安全性和相关基础研究以及临床应用中都有了较大的进展。现就ART相关进展概述如下。

1 辅助生殖技术安全性的研究进展
1.1 辅助生殖的子代安全性研究
由于ART各项技术的直接临床应用前均无充分的实验室基础研究背景,它的出现在解决人类诸多生育问题的同时,人为地引入了大量非生理性的操作,在生命形成最关键、最易受外界影响的受精和胚胎早期发育阶段对生殖过程进行干预,随着ART出生子代人数的增加,这一特殊人群与自然妊娠获得的后代相比,是否存在更大的健康风险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关注的问题。近期,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ART子代出生结局、生长发育和相关疾病方面。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对ART子代的出生缺陷进行描述。1987年,Lancaster指出IVF婴儿发生神经管畸形和大血管移位的比率增加,但由于本身研究对象人群量小和统计学方法的缺陷等,多数情况下将出生缺陷的主要原因归咎于ART实施后的多胎妊娠和父母的背景因素,如年龄、精神因素和存在的疾病状态等,而非ART技术本身。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即使排除ART之后的多胎因素和亲代的不孕病史,ART子代的出生缺陷风险仍增加。2002年,Schieve 等[1-2]两次的临床数据中均发现ART后代,即使是足月单胎婴儿,低出生体重及极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都较高,为自然妊娠婴儿的2.6倍;在2004年Jackson等[3]和Helmerhorst等[4]的系统评价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而且2020年,来自美国3个州近十年约190万单胎新生儿的调查中发现[5],ART获得的子代早产率明显高于自然妊娠组aOR 1.24 (95 % CI, 113, 137), aOR 160 (95 % CI, 150, 1.70), aOR 1.49 (95 % CI, 1.35, 1.64),和aOR 1.26 (1.12, 1.43)。同样在双胎妊娠结局中,McDonald等[6]在2014年的Meta分析中指出,在控制母亲年龄及其他因素后,IVF双胎早产发生率(RRI 23.95 %, CI:1.09~1.41)及低出生体重率(<2 500 g,RRI 1495 %, CI:1.04~1.22)较自然妊娠双胎显著增高。但由于新生儿医学的发展,即使在早产率和低出生体重较高的情况下,新生儿的死亡率ART组与自然妊娠组并无差别。
在先天出生缺陷中,ART,特别是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技术,免去自然受精过程对精子的筛选,使得一部分存在遗传异常的精子受精并发育,将此类缺陷遗传给下一代。而母亲的不孕因素,包括生殖相关疾病和盆腔炎症等可能是导致母亲相关妊娠并发症发生的原因,从而导致早产等子代不良结局。因此,亲代不孕背景可能是导致 ART 子代异常的基础。2005 年,Klemetti 等[7]在芬兰的一项大型研究将 IVF(包括常规 IVF,ICSI 和FET)、其他 ART 与自然妊娠子代的先天畸形发生率进行比较,发现 IVF 子代中单胎男性与对照组相比先天畸形率(特别是泌尿生殖系统和肌肉骨骼系统畸形)增高,而其他ART 子代中单胎女性心脏畸形发生率增高。其他亚组与对照组相比,风险轻度增高。
近年来由于表观遗传学研究的兴起,有较多动物研究发现ART相关配子或胚胎体外操作或培养会引起子代表观遗传修饰改变,主要为印迹基因区甲基化修饰异常导致基因印迹异常。典型的病历为多项研究报道ART出生由基因印迹缺陷导致的 Beckwith-Wiedemann综合征(BWS)和Angelman综合征(AS)患病率升高。我国科学家黄荷凤等也对ART治疗的配子及胚胎的表观遗传学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导致表观遗传学异常的可能原因有:夫妇双方的不孕遗传背景、超促排卵、体外操作及培养。
1.2辅助生殖技术与母亲安全性
在ART技术实施中,有关母体安全性中讨论最多的即是超促排卵之后出现的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 OHSS)对于女性全身和局部的影响;以及ART治疗后多胎妊娠相关的母胎产科并发症,但关于通过ART获得妊娠的相关母体妊娠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报道较少并有争议。2007年,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Schieve 等[8]的临床观察中发现,ART 存在多种妊娠并发症和分娩并发症发生率增高,如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出血、胎盘早剥、早产等,严重影响新生儿结局,这种结果可能与不孕症本身的慢性疾病状态有关。2009年,来自澳大利亚的Healy等[9]也对IVF/ICSI单胎妊娠出生的母婴结局进行回顾性分析,指出即使是单胎ART获得的妊娠,发生产前和产后出血的概率也增加,其发生与超促排卵、子宫内膜异位症、激素应用等因素相关,因此推测胚胎种植前后子宫内环境的改变是引起后期妊娠并发症的关键因素。2005 年,Shevell 等[10]对ART单胎妊娠进行分析,发现 ART 组子痫前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和剖宫产率均较自然妊娠组增加,并认为由于 ART 的妊娠和绒毛膜发育起始于体外培养,这种胎盘早期的发育环境改变和本身异常发育会导致这些胎盘相关性并发症的发生率增高。但最近仍然有学者指出 ART 不增加胎盘相关性妊娠并发症包括子痫前期、胎儿生长受限、胎盘早剥和死产等的发生率[11]。因此,目前的结论并不统一,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关于 ART 是否伴随高发的母体妊娠期并发症,需要进一步大量的临床研究才能得出。
2 临床技术研究的进展
2.1促排卵方案观念的改变
近年来随着生殖医学理论和实验室技术的进步,对于患者在进行IVF治疗过程中的安全性评估越来越重视,对于卵巢储备功能的评估也有了抗苗勒氏管激素(anti-mullerian hormone,AMH)、基础窦卵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AFC)、基础促卵泡素(basic follicular stimulation hormone,bFSH)等一项或者多项指标联合预测方式,对于卵巢反应性给予更加客观评价,选择个体化控制性卵巢刺激方案(individual controlled ovarian stimulation,iCOS)以给予患者更精准的促性腺激素(gonadotropin,Gn)起始剂量和更适合的促排方案,预防或减少OHSS等医源性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2.1.1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hin releasing hormone, GnRH)拮抗剂的应用在国内,尽管多数中心针对卵巢正常反应者首选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onadotrophin 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 GnRH-a)长方案,但随着新一代GnRH拮抗剂的广泛应用,拮抗剂方案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拮抗剂方案缩短了治疗时间,对于患者更加方便,舒适且经济,减少了OHSS发生以及促排卵的不良反应,同时该方案雌激素水平的降低也有利于胚胎种植,目前该方案的运用已从卵巢低反应人群逐渐扩大到了年轻、卵巢正常反应及高反应和低反应等人群。特别是在高反应人群和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使用GnRH-a进行扳机,重度OHSS的风险可以从3 %降低到0~2.6 %[12]。
2.1.2重视卵巢储备功能下降患者的治疗临床方案和观察随着我国全面二胎政策的开放,高龄妇女(>35岁)要求借助ART完成二胎生育的患者越来越多。卵巢储备功能不良和低反应患者在此年龄段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相对于正常反应人群,促排卵方案的制定难度更大。目前微刺激方案与自然周期方案在卵巢功能下降、卵巢低反应患者中的应用成为热门话题,不少报道认为卵巢低反应患者采用微刺激方案能够取得较好的获卵率及临床妊娠率。但也有专家认为,在基础FSH水平增高的卵巢低反应患者中应用微刺激方案效果不佳。近来有报道认为,卵巢低反应患者采用自然周期其疗效与控制性超排卵(controlled ovarian hyperstimulation,COH)无显著差异,对于>40岁的高龄患者自然周期与COH获卵率几乎无差异,但自然周期无须接受外源性Gn,减轻了由于卵巢低反应屡次失败反复促排卵的昂贵医药费及沉重的心理负担,是可取方法之一[13]。无论哪种方法都须经过深入研究,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发挥每种方案的最大效能。
2.1.3高孕激素作用下的COS黄体期促排卵是近年来开始被尝试的一种新的促排卵方案,在国际上该方案被命名为“Shanghai protocol”[14]。该方案的发明者上海九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匡延平团队在正常反应、高反应和低反应患者中均做了此方案的尝试,结果发现其能获得较好的临床和实验室结局。特别是对卵巢反应不良患者实施黄体期促排卵可增加获卵数、成熟卵子数、受精卵数以及冷冻胚胎数,从而为提高妊娠率提供了可能。但该方案对获卵质量影响的相关临床应用及动物实验研究较少,其临床应用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2.2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植入前遗传学筛查的巨大进步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技术主要应用于胚胎性别诊断、单基因疾病和染色体结构与数量异常疾病的诊断,少数多基因疾病在有确定家系样本参照下,也可以进行PGD尝试。
1990年,andyside等在国际上首先创立了PGD/植入前遗传学筛查(preimplantation genetic screening,PGS)的临床应用,早期的遗传学诊断方法主要为聚合酶链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PCR主要用于单基因遗传疾病的诊断,FISH则主要用于检测染色体异常以及胚胎性别。PGD的主要适应证是单基因疾病、遗传性的染色体异常和X-性连锁疾病[4]。早期由于技术的限制,PGD的受用面较窄,但随着微阵列及全基因组测序等综合分析技术的临床应用,大大促进了植入前胚胎遗传学检测的发展。目前用于临床的新方法有:比较基因组杂交(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CGH)、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芯片、新一代测序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全基因组扩增(whole genome amplification,WGA)及其下游技术,包括简并寡核苷酸引物PCR(degnerate oligonucleotide primed-PCR,DOP-PCR)、扩增前引物延伸反应 PCR(primer extension preamplification-PCR,PEP-PCR)、多重链置换扩增(mutiple dilacement amplification,MDA)以及多次退火环状循环扩增技术(multiple annealing and looping based amplification cycles,MALBAC)。
2013 年人类生殖和胚胎学协会的年会上,Wells 等[15]汇报了首例NGS-PGS妊娠成功的病例;同年,华大基因与湘雅医院也报道了NGS检测囊胚的PGS成功病例[16]。2014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诞生了世界首例和第2例MALBAC扩增测序的PGD婴儿,分别诊断了遗传性多发性骨软骨瘤和X-连锁少汗型外胚叶发育不良。2017年4月,以徐娟娟[17]为主的研究团队报道并验证了一种新的无创染色体筛查方法(noninvasive chromosome screening, NICS)。此方法基于对游离到囊胚培养基中的人类囊胚DNA进行基因组测序,通过MALBAC全基因组扩增,对42个囊胚培养基进行高通量测序,证实了囊胚培养基与对应胚胎的染色体异常检测结果的高度一致(灵敏度0.882,特异性0.840),该方法避免了以往方法的胚胎活检,有高度的准确性和无创性,显著增加了其应用的安全性,在临床应用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这些技术的成功临床应用,引领着PGD/PGS技术在人类遗传性疾病的研究中迅速发展,为避免出生缺陷起着重要的作用。
ART在不孕症的治疗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对特殊人群的作用,如卵巢储备功能不良、需要进行PGD的患者,临床应用的有效性逐渐增大。但由于其安全性尚待更大规模和样本的观察,应用中仍然应严格掌握适应证。